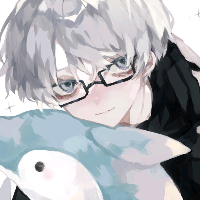在开始之前,首先呻吟一下,作为现场唯一一个修这门课的大三老狗,与年轻面孔的讨论总是激发我感叹:作为DDL战士(战神)却又一丝不苟。换作一堆大三老狗来做的话,不是一个人带飞就是LLM带飞。和这么一群已熟悉学校生存规则却又不将自己深陷自我轨迹的一群人一起做事确实给我带来一丝安全感。闲话就不多讲了,毕竟DDL在即了。
《记忆的性别——农村妇女和中国集体化历史》这本书站在女性视角,讲述了在中国自“解放前”到改革开放的时间链上生活和生产的变化或变革。通过对陕西农村地区妇女的走访,用农村女性的记忆与叙述,引导那些远离话语中心而被默认为“无历史感”的群体——农村妇女,在这本书构成的情境中成为历史的主体。
本书的记录以农村妇女在这段时期中的身份转换为分野,基本沿时间线展开。在解放之前,农村妇女处于得不到保护的难民状态。她们被迫走出家门,外出去耕地、去出售纺织品、去乞讨、去逃难,“养家都指望着她,家里没人”。她们在这一时期的状态在书中用“恓惶”来形容,然而却在解放的初期被要求以“封建”来“诉苦”。解放初期,国家为了突出“反封建”的叙事,鼓励妇女在“诉苦大会”上讲述自己在过去被禁锢于狭窄的内闱的故事,却忽略了妇女早已被迫走出家门的事实。这不仅反映了妇女实际劳动贡献与社会认知间的割裂,也显示了国家对农村妇女的记忆进行遮蔽,以推进事件或运动的进行。
在解放初期,土地改革推行,婚姻法颁布,扫盲运动启动,妇女们以新的人民的身份参与到国家政治与日常生活中。她们参与领导,作为积极分子,生活出现新的气象。妇女被鼓励婚姻自由,然而,矛盾的却是,妇女领导者的选择却常常让步于传统妇德,只有“守节”才能得到信任。这部分归咎于男性几乎垄断政治的现状:在男性视角中,为了推进男女平等,让女性进入领导层,这本无错,但是他们忽视了女性视角中要成为领导所要付出的代价;还有部分原因被“一切社会主义都带有地方性”解释:在新一套理论从国家流向地方时,为了保证理论正常运行,“服水土”,不得不将其嫁接在地方性的意识形态上面,后面的集体大食堂的破产也可引咎于对地方乡土社会结构的漠视。
在文化生活领域,国家推行扫盲班、冬学、歌舞戏剧的文化活动,鼓励妇女学习文化,一定程度上使妇女们体验到乐趣与自信,并提升了妇女们参与土改等运动的积极性。可惜,妇女们的学习时间被农业生产、家务、整治活动等挤占,学习难以为继。冬学为妇女走出“封建”家庭场所提供了一种初步的方法,然而要让大部分成年妇女都识字依然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妇女没有同等的文化地位,自然也未能真正改变男性主导的话语权结构。
接下来(1953至1957年),农业生产需求上升,农业合作化推进,工分制度确立,在此后很长一段集体化时期里,农村妇女身上农民的身份持续,涌现出许多劳动模范。作为农民,在公领域妇女加入合作社,参与农业生产活动,妇女们不再向过去那样被禁足,而是可以光明正大地加入农业生产。妇女为国家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适时有“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宣传口号。然而,公分制度下的性别歧视仍非常严重,付出同样的劳动,男性能获得10工分,女性只有7公分。而在私领域,社会默认地将家务劳动与育儿任务分配给妇女,有她们全权负责,却不将其视为一种劳动,变相的成为了一种无偿劳动,许多妇女不得不晚上织布到天亮来弥补工分。建立在社会性别差异基础上的劳动分工和薪酬差距都被广泛地视作是理所应当的。
调整与动荡的时期,国家发生经济调整、计划生育、文化大革命等历史事件。女性作为劳动者、接生员、母亲,她们的生活也受到影响。
在农村,女性的生育总是受到关注。在集体化进程中,女性在生育的过程中是否得到所需要的关怀、呵护与科学的照料呢?答案是有的。国家推广新式接生,为农村安排了新式接生人员,新式接生工具与新式接生方法,改变了过去封建社会中分娩“羞耻、肮脏、可耻、罪恶”的观念,消去了妇女们的恐惧与痛苦,妇女的生育境遇大幅改善。然而,“国家没有一直关注妇女的生育健康,而是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增加农业产出以发展工业、动员妇女劳动上,而非改变她们的生育生产状况上。
在这一时期,女性身上同时出现了两种符号:母亲与模范。社会一方面希望女性承担同男性一样的劳动,作为革命的、劳动的模范,另一方面又要求女性承担家务劳动与育儿任务,具有母亲的美德。女性在两重重任的撕扯下成了革命与美德的容器,自身的诉求嘶哑、被牺牲。
公共劳动中女性要挣工分,而私人领域,她们的境遇仍未得到改善。同时,国家未有效建立托育系统,不少妇女回忆到下田劳动时,她们不得不将孩子拴在树上。这一切,反映了国家对妇女成为社会主义劳动者与作为传统母亲的苛刻要求,而妇女也在两种角色的重任间痛苦挣扎,无暇诉说自己的需求。
为鼓励妇女参与生产,妇联和农业干部“发现并培养”劳模,通过技术培训、演讲辅导和媒体宣传将其树立为典型;她们被要求掌握如棉花高产等技术能力,保持政治忠诚,作为地方榜样,并频繁参会、接受采访,作为政策的传声筒,在忙碌中脱离实际生产。劳动模范成了一种政治的工具,需要表演女性的革命形象。她们被宣传,却牺牲了真实的生活诉求。
1978年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核心家庭兴起,社会迎来新的生机。老一代妇女逐渐衰老,慢慢从历史舞台中退去,作为对曾经集体化历史记忆的叙述者,这些妇女的记忆如今面临着哪些困境?改革开放后,记忆迎来了巨大的断裂。市场经济否定集体化记忆,年轻人看不见叙述者们曾经的贡献;老年妇女陷入“赡养危机”与“记忆失语”,儿女进城,留下空巢老人。故事得不到言说,贡献得不到认可,记忆得不到传承,叙述者们面临着现代性“冷漠”。她们从集体劳动者,家庭照顾者,最终成为了记忆的边缘人。记忆,成为她们抗争现代性“冷漠”的最后武器。
她们在回忆中强调自己的美德和贡献,强调集体化初期生活的改善,强调乐观发展的视野,与此同时选择性地遗忘“大跃进”等痛苦的回忆,来构建一套“进步”的叙事。
以上便是整本书的大致内容,再次感谢所有的小组成员对整本书内容的准确把控;由于本人的社会学和语言功底有限,这里尽可能引用来自北大马院博士冯嘉馨的《“地平面”下的历史》来解读。这篇作者似乎是美国的一个女权作家,她以农村女性的独特视角讲述了中国上世纪发展的部分历史(解放、集体化、大跃进等等)。
一个特定群体在特定历史时代的氛围和心境,底层鲜有人注意的琐碎生活、心态情感、文化观念,都属于那些藏匿在地平面下的、被遮蔽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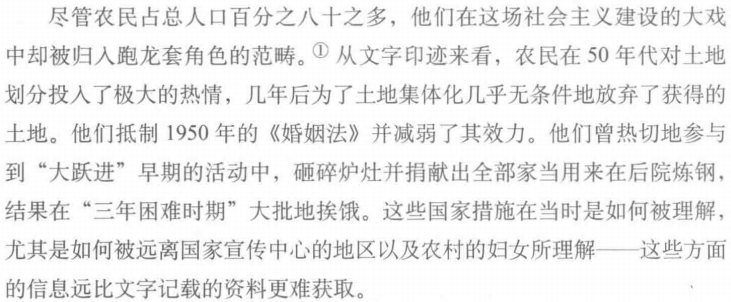
从这本书或者说是作者的想法出发,这本书在引导那些远离话语中心因而被默认为“无历史感”的群体在这本书构成的情境中成为历史的主体。
从书名来看,记忆也是有性别的,不同于国家视角、集体视角以及男性视角的以各种运动组成的“正史”,农村女性的记忆却是带着另一种情境,她们的记忆存在着时间的“错位”与“褶皱”。
在书中,作者只是用悬问匆匆带过(虽然我不这么认为,可能因为我跟学姐的社会学认知深度不在一个level上):
静默、对时间的省略和爆发性的记忆是创伤之后的结果吗?还是去政治化的结果?抑或是极度疲惫和忙于日常生活的痕迹?
冯嘉馨学姐从社会学视角对此进行了解读:
传统农村社区的记忆:“无事件境”——一个事件与其他事件混杂在一起时,并且经常互涵和交迭,呈现的是一种循环的时间观。因而,村民的记常常是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区分的模糊区域。
女性记忆的特点:更多体现出具身性,更多讲述与切身体验相关的事情、与日常生活不同,打破她们绵延的生活状态的事件。“农村妇女习惯用十二生肖、阴历月份、孩子出生等对之具有重大意义的生活事件来作为确定时间的标识。,从而形成了偏离国家话语的时间观”。农村妇女的生活方式偏向于封闭,没有现代社会多元的身份认同,而是停留在单一的、被分派的角色之中,加之以社会交往和公共活动的匮乏。
日常逻辑:农村女性的叙述或记忆呈现出一种“总体物质水平得到提高的故事”,她们对于这一方面的希冀抚平了她们的一些记忆,她们的记忆是被这条主线索引的。
然而,我并不想从社会学的视角对记忆的“褶皱”进行太多解读。书中的一些主题和思想映射到当下时,却也能透过历史解析现在。
农村女性“被解放”到国家需求之中,却湮没于主体叙事,“从一种被支配状态进入另一种被支配状态”,“从家庭与宗族的附属品成为集体和国家的工具的过程”。政治口号下,妇女们能顶半边天,却实则顶着公领域与私领域负荷的两重天。妇女们得到的是劳动力的解放,而单纯地作为“女性”并未得到完全解放;集体化将妇女从家庭推向农田,政策改革只触及表层的分工,但未颠覆性别权力结构。她们的劳动成为国家现代化的“隐性代价”。
贺萧用农村妇女的口述史,有力冲击了国家记忆的力量,打破了国家线性叙事。我想,在我们飞速发展的同时,理应去思考,现代化究竟落脚于什么?福祉究竟要赋予谁?时代究竟能不能以“集中发展力量”为由将个体的牺牲视为理所当然?历史究竟应不应该抹去一个群体的记忆?当政治真正地以“人民”为中心时,怎么做到不让“官方视角”遮蔽“边缘化视角”?
延伸至今,现代化发展的潮流下,个体被赋予特定的时代符号,无可奈何为时代注脚。三和大神、外卖员、失业人群、无业应届生、日本上世纪末“消失的一代”...这些个体被裹挟着成为标志分明的群体,却终将在主体叙事中被一句话带过,或是成为过渡时代的一个逗号。
把自己当作“螺丝钉”的是无产阶级、劳动阶级的觉悟,但把劳动者当作“螺丝钉”的是一种形式的压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构想的社会主义中,发展的终极目标是“人人都能从事自己热爱的工作”。如果说在百废待兴的时期,发展是无产阶级成长的第一要义,那么在飞速发展、日渐富裕的当下,发展能否更多以“人”为根本。在生育率低下时,在国家、上层建筑的视角中,鼓励年轻人生育无可厚非;但在青年人视角中,居高不下的房价,越来越高的育儿成本,甚至是飘忽不定的工作,都成为了很多底层年轻人在结婚和生育面前望而却步的大山;部分公知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底层,脱离了群众,他们高傲地用最正确的政府视角俯视社会底层攒动的人头,却不愿下来看清任何一个人的脸,不愿与任何正为生活奔波的人交谈,更不愿穿上黄色的工服,切身体验底层人民被生活、被时代尘埃所吞噬的无力感。
再看那些中年失业者,在十年或二十年之前,他们或许还在广东、浙江、江苏等地的工厂里为中国融入世界经济做出努力,如今,他们却已被贴上“低学历”、“廉价劳动力”的标签。或许未来,在官方对这一时期的记事中,我们在“双碳目标”、“抗击疫情”、“科技飞速发展”、“房地产崩盘”、“经济发展停滞”的这些词语中,很难再找到这一群人,至少在目前的教科书中,我们对他们的所有了解止于“丰富的廉价劳动力”。可谁知道,他们曾作为“劳动者”投入到国家飞速建设中,作为“父母”撑起了经济下行下中的小家,作为“青年”拥有并实践着自己的梦想,作为“人”参与到社会中去。他们作为社会中被边缘的一方,在需要时贡献血汗,在不被需要时却不能得到好的安置。
我不知未来将于谁手中,我只顾芸芸苍生。